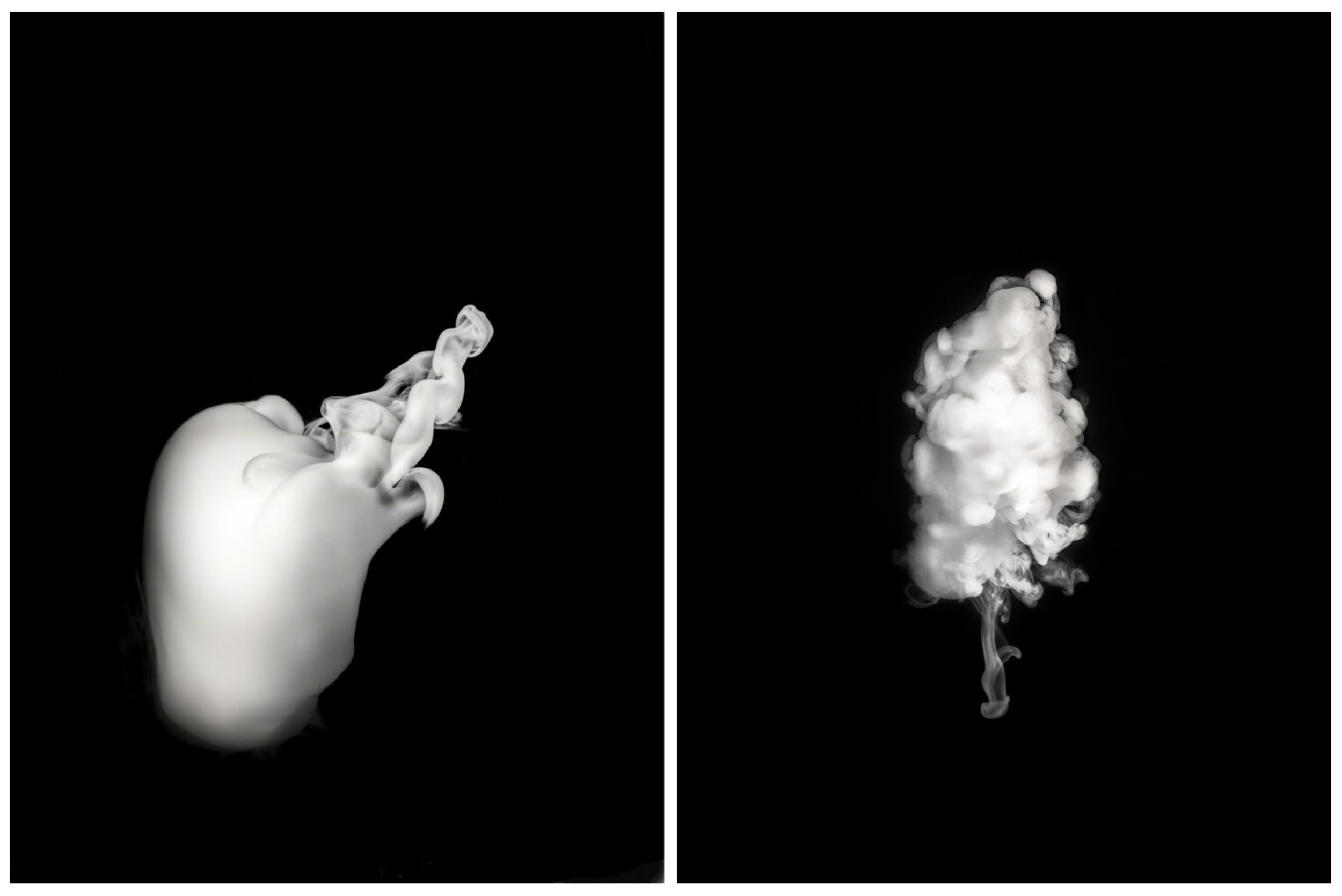「平日我們見到的事物都是立體的,但在相片中卻是平面的,Fotomo作品的特別之處是將平面的事物變回原本的立體效果。」藝術家葉家偉(Alexis)從事Fotomo創作十五年,將鏡頭對準香港街頭不斷消失的小店與排檔,再以手工剪裁及拼貼成立體的攝影浮雕作品,以獨特手法重現港式老店風情。

影像錯落有致 照片更有生命力
顧名思義,Fotomo由foto與model結合而成,概念源自日本攝影師糸崎公朗(Kimio Itozaki),他用相片結合模型的手法,以立體的模型效果,更寫實地展現真實世界。身為中學視藝老師的葉家偉,2004年帶領學生參觀糸崎公朗的Fotomo展覽後深受啟發,一方面嘗試在課堂上教導學生製作模型,另一方面慢慢演變成個人的藝術創作,「糸崎公朗是將平面的日本街景相片摺叠成立體的模型,我則是通過多層平面的影像拼貼成浮雕效果。」他很快以港式Fotomo闖出一片天地,作品《藍屋》入選2005年香港藝術雙年展,另一作品《香港影像:花園街》則獲2009年香港當代藝術雙年獎優秀作品獎。
葉家偉說,這種創作手法比較適合畫面豐富的場景,如老店及排檔等,多年來,他的足迹遍及港九新界,創作過逾百件作品。「很多時我們對這些店舖習以為常,往往不太留意,然而當其變成一件精緻的作品時,才會去細心欣賞這些事物。」他作品中的生果檔、士多、雜貨店,是一件件充滿細節而富有層次感的作品,少則四五層,有的可多達十層,突出街頭小販獨特而創意的展示手法,立體浮起的影像錯落有致,令照片更有生命力。
背後的每個細節,都是他耗時兩星期一手一腳拼貼的成果。葉家偉的作品某程度上讓我們得以重新發現身邊的美好事物,去重新了解這些微不足道的故事。喜歡紀實攝影的他,拍攝時樂於了解老店背後的故事,有歷經三代的遮舖、有逾半世紀歷史的灣仔愛群理髮店,可惜的是,像這類有特色的店舖現在已買少見少,有的因加租、有的檔主退休、有的被時代淘汰、也有的因重建而消失,「朋友說我的作品是『死亡筆記』,許多拍攝過的店舖都已消失。」重建的屋邨、面目全非的利東街,所有的回憶與美好,均抵擋不過時代的巨輪,他不無感慨,只能在立體的作品中緬懷。

嘗試合併兩舖 並置效果時空交錯
雖然他坦言自己最喜歡陶瓷創作,不過多年來也一直探索Fotomo的創作方法,最新嘗試是將兩間不同空間的店舖合併在一起,愛群理髮店舊址原在灣仔,旁邊的志記配匙是在彩雲邨,時空交錯的並置效果頗有趣,畫面亦毫無違和感。「作品中正在理髮的是我的兒子,其實真實的理髮店在紅磡,然而卻能完美地融入這個畫面。」另一個例子是在赤柱的合益士多,掛滿沙灘波的士多場景是在夏天拍攝,而前景穿着厚衣的人物明顯可見是冬天,畫面中小朋友指手劃腳的效果,正好與時空交錯的店舖產生互動,也令作品更生動有趣。
重構 RECONSTRUCT
日期:8月9日至9月15日
時間:星期三至日(11am至6pm)
地址:上環磅巷28號Blue Lotus Gallery
原文見於果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