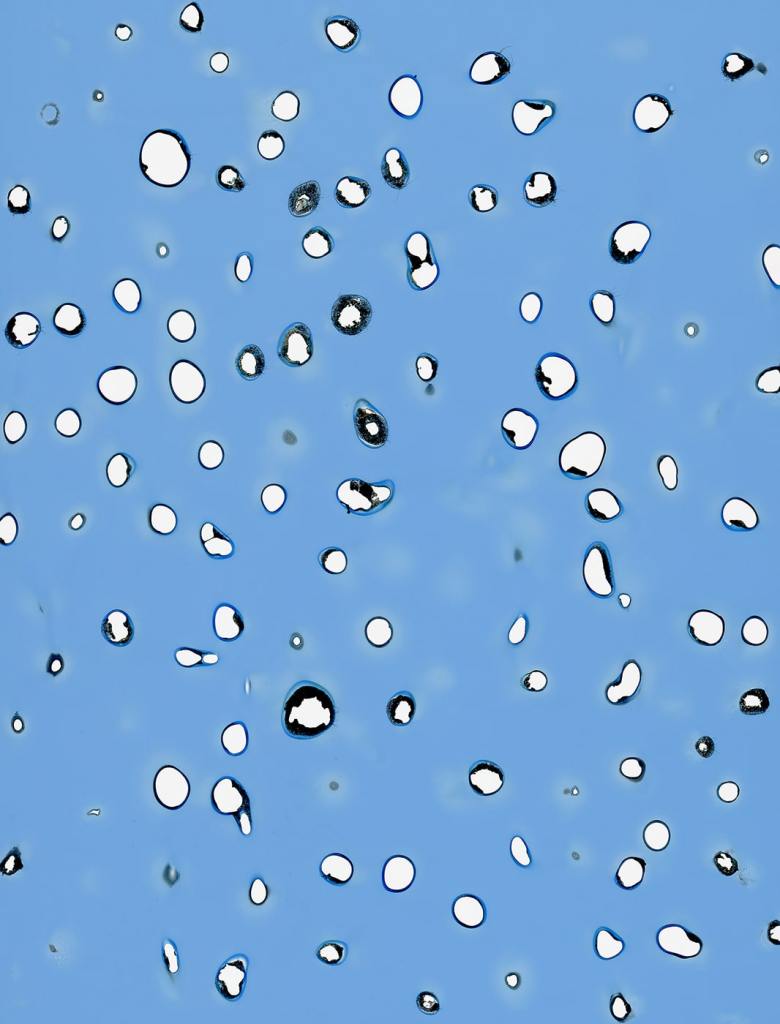「西環碼頭不只是打卡勝地,更是附近居民及其他人生活空間的延伸,就像一個面對着維港的公共大露台。」居港意大利攝影師Pierfrancesco Celada談起月前關閉的西區公眾貨物裝卸區(俗稱西環碼頭),心中不無可惜,自從2016年在Instagram上開設賬號「Instagram Pier」以來,他在西環碼頭拍攝約三萬張照片,記錄大家在這裏度過時光或自拍時的花絮。他形容:「如果西環碼頭是他們的舞台,那麼我的賬號便是他們的後台。」

Pierfrancesco的暱稱是Pier,某程度上也預示他與碼頭的緣份。當時家住堅尼地城的他,覺得附近西環碼頭的景色很漂亮,也很有趣,他發現許多人每天都在這裏做着相同的事情,釣魚、散步、放狗等,這種重複的日常令他深感興趣。最初一兩年,他幾乎每天都在碼頭拍攝數小時,後來遷居大嶼山後便不再那麼頻繁,尤其是去年疫症爆發期間,哪想到碼頭會暫停開放,Instagram Pier的計劃也隨之告一段落。最近,他舉辦同名展覽及推出同名攝影集,也算是這個拍攝計劃的回顧與總結。

蜘蛛俠現西環碼頭 天空之鏡靠水桶
展覽現場的牆上,密密麻麻地貼滿1,500張在西環碼頭拍攝的照片,在貨櫃、竹架及維港的景色之下,男女老少做着不同的事情,釣魚、自拍、做運動、看日落、跳舞,連攝影師的妻兒也曾出現在相片中,承載着許多他的回憶。「香港的公共空間都有很多規條,很多事情不能做,西環碼頭作為一個公眾地方,是很自由及獨特的,這裏是大家生活空間的一部份。」

西環碼頭是拍攝日落的熱門地點,許多人專程過來拍攝婚紗照或維港景色,當中不乏有趣畫面,為令照片看起來比較「特別」,許多人會開心跳躍、攀高爬低、做一字馬、打觔斗,甚至以蜘蛛俠的裝扮前來拍攝。這裏也有「西環天空之鏡」的外號,原來營造鏡面效果的水灘,有時是人們自帶水桶從維港裝水的「用心良苦」。這些精采照片背後的幕後花絮,統統記錄在Pier鏡頭之下。

猶如無形社區中心 自備電視睇粵劇
「我是以觀察者的身份拍攝的,對人們在這個空間的行為及如何表現自己深感興趣,這些照片也記錄摩登都市的另一面。」他說大部份人會在黃昏時前來拍照,夜晚則比較多街坊,散步的、做運動的,還有跳舞的姨姨們,街坊們有時更會自攜電視機一齊圍着看粵劇,猶如一個無形的社區中心。「這是一個很有凝聚力的公共空間,我很好奇碼頭關閉後,他們現在能去哪裏?」隨着碼頭悄悄關閉,他希望大家可以從展覽中重溫對西環碼頭的回憶。

在拍攝碼頭的同時,他也收集其他人在西環碼頭拍攝的照片,兩者形成有趣的對比。「可能大家都在Instagram上看過相同構圖的照片,很多人來這裏都是拍攝類似的指定動作及背景,往往同一個位置拍攝很多張照片。」其實不只是西環碼頭,香港其他打卡勝地也有類似情況,這某程度上是對Instagram打卡文化的一種批評,令人反思社交媒體對生活的介入及影響。「若從另一方面看,這些人在這裏是很愉快的,他們向人展示生活中開心、美好的一面,其實也沒有不妥。 」
Instagrampier
日期 : 即日至7月25日
時間 : 12nn – 7pm (二至日)
地址:WMA Space(中環永和街23-29號俊和商業中心8樓)
原文見於果籽
·如果你認同文字有價,歡迎透過PayMe( payme.hsbc/photogstory )支持「顯影」。